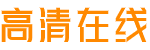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并不试图对《夜》给出 “完整” 的看法,或者说不从现代性、建筑及空间等传统角度出发,而更希望从另外一个侧面去进入它。这始于对《夜》中某个细节的观察,而当观察变得更进一步的时候,一种以相对融贯的解释来对所有被知觉到的现象进行组织的期望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在《夜》中,我们时常感受到一种困惑,这或许是对人物关系走向的不解,它一方面来自于对机械因果式的叙事的抛弃——我们永远只能知道不同的(但大多时候意味着破坏的)事件的发生,却无从得知其发生的原因,正如派对上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样,不管是对于它自己,还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就那样发生了,若试图找到其原因,最终只会是毫无所得。而另一方面,这种困惑也来源于演员在表演上与“真实”的背对——至少,在安东尼奥尼著名的三部曲中,我们看不到即兴表演的迹象,也几乎不能从人物身上感受到自然的情感流动(《奇遇》也许是个例外,在其中的某些时刻,维蒂能够从容器般的演员存在中得到解脱,尽管这种超越只是暂时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夜》仅仅是一种无可复加的模糊,或者说只是某种意义上的神秘与不可知。事实也许恰恰与此相反:婚姻中情感关系的变化,实际上与这部电影大量使用的深焦镜头一样清晰。当然,这种清晰性不来自于故事,更确切地说,我们并不能通过角色的台词而把握到关系真正的流变。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真实的而非被口述的关系,是因为对关系中作为主体之一的 Lidia(片中的妻子)的视线与声音间的此消彼长有所感知。
而我们之所以能捕捉到这样一种强烈的变化,其原因也许首先是:妻子 Lidia 这一观看主体的建立发生于电影时间的前端。当处于这样的位置时,这样一种建立便天然地拥有一种作为“在先的印象”的坚实性,以至于我们甚至会将 Lidia 的主体性与其视线联系起来。在医院这一空间(也许是片中首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中,人物第一次产生交流,然而夫妻间的言语交谈却几乎是完全空白的;与声音上的虚无相对,经由 Lidia 投出的(作为一种关系的)视线却总是实存于空间中,并不断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
比如,在医院电梯中,夫妇间保持沉默的同时,Lidia 两度向她的丈夫 Giovanni 投去目光:

 第一次建立妻子视线的场景——电梯内
第一次建立妻子视线的场景——电梯内而当他们出现在病房时,Lidia 的视线在两次重要的镜头运动中获得了极强的在场感,以至于无法被任何在镜头背后的观看者所忽略。其中,第一次镜头运动是摄影机与 Lidia 这一主体的运动线保持平行的横移:
 与被观看者处于不同的焦平面,由此建立起一种观看的秩序
与被观看者处于不同的焦平面,由此建立起一种观看的秩序 视线移向另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对上述的秩序进行强化
视线移向另一个被观看的对象,对上述的秩序进行强化 与观看者保持一致运动的横移镜头在此时所展示的被观看对象也与观看者的对象达到完全的一致(当然观看者的视线也必不可少地被展示出来)
与观看者保持一致运动的横移镜头在此时所展示的被观看对象也与观看者的对象达到完全的一致(当然观看者的视线也必不可少地被展示出来) 横移结束时,区分开观看者与其观看对象的,不仅仅是原先的焦平面,还有观看者身后的窗帘与作为被观看者背景的窗口的区隔
横移结束时,区分开观看者与其观看对象的,不仅仅是原先的焦平面,还有观看者身后的窗帘与作为被观看者背景的窗口的区隔第二次镜头运动则是出现在不久之后的以 Lidia 的背面为前景的跟拍镜头,此时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也许是最为清楚的:

 与上一次运动不同,这一跟拍镜头更以面孔的朝向对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作出区分,且因为此时的摄影机视线与观看者的视线形成了交汇,此时 Lidia 视线的力量较于之前是更为强化的
与上一次运动不同,这一跟拍镜头更以面孔的朝向对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作出区分,且因为此时的摄影机视线与观看者的视线形成了交汇,此时 Lidia 视线的力量较于之前是更为强化的如果说在医院的室内戏中一种对视线的强调使得我们甚至将观看的能力/权力视为 Lidia 的存在的本质,而观看者本身又是拒绝被观看的,那么在这之后,我们所能察觉的便是这一观看主体的本质所受到的挑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夜间派对上来自另一名男性的视线:



在这一场戏中,画面左侧的陌生男性( Lidia 一女性旧友的朋友)朝向 Lidia 的视线,在他出现时便也一同出现了。而当 Lidia 反应过来自己正在被观看时,她的惊慌程度——若仅借助于表层的文本——便几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而既然她知道,在当时的场合下出现我们通常认为的危险之可能性不大,那么真正使其产生如此大的惊恐的又是什么呢?若联系之前所提到的,即 Lidia 是作为观看主体的存在,那么她在此时的反应便也不那么异常了,毕竟这样一束来自他者的目光使其主体性受到了威胁。当然,此时两人中何者处于优劣势,也借助光线在双方面孔上的明暗对比及二者所处的空间位置而得到体现:陌生男性与光源更为接近,在某一时刻其脸部甚至出现了与周遭环境极不协调的明显的面光,相对地,Lidia 的脸孔却几乎始终被大块的阴影所覆盖;与男性所处的大面积的地平面相比,她所站立的位置却是在地面的边缘,以至于似乎其再往前踏一小步都会导致自己落入水中,而当其试图摆脱视线的时候,其同时也是在离开这一 “危险” 的位置。
而在电影的最后一场戏中,Lidia 的观看主体性所受到的解构与破坏也许最为强烈,因为在这数分钟内便两次出现了其丈夫的 POV 镜头,而在此之前的部分中,这类镜头几乎没有出现过。
 丈夫第一次以其自己的(有别于妻子的)看的方式看向妻子
丈夫第一次以其自己的(有别于妻子的)看的方式看向妻子 之后不久出现的第二次类似的目光
之后不久出现的第二次类似的目光与 Lidia 这一观看主体的解构所相对的,是其人声(voice)的凸显。Lidia 的被观看实际上是在其朗读时所发生的,而正如 POV 镜头在片中那样,朗读也是相当罕见的(也许是片中的唯一一次)。尽管对书籍的展示与翻看在片中数次出现,但却没有任何一次,文字是被用来朗读的:在病房中,生病的好友与 Giovanni 谈及后者的文学作品,但这一谈论本身就只是外部的,换言之,这实际上只是在将作品本身对象化,由此也不可避免地生出一种距离感;当丈夫所写的书出现在派对上时,除了 Valentina 外,几乎没有人动过它( Giovanni 对此还颇有微词),然而即使如此,在 Valentina 与这些文字所发生的关系中,也并没有任何人声的在场:
 Valentina 的默读被妻子所目睹
Valentina 的默读被妻子所目睹值得注意的是,朗读早在派对上就以某种潜在的(因此不仅仅是与片尾妻子的朗读相对照,且更是为一种演进的脉路作出了第一步勾勒)状态出现,或者说被我们所知:
 Valentina 向 Giovanni 提议一起朗读(在该语境下 “read” 也许不应解为 “默读” )前面提及的文学著作,然而朗读的动作并未真正发生
Valentina 向 Giovanni 提议一起朗读(在该语境下 “read” 也许不应解为 “默读” )前面提及的文学著作,然而朗读的动作并未真正发生由此我们大致产生这样的印象:相比起派对上的其他人,Valentina 与文字所发生的关系更为亲密;然而,似乎又有另一种暗示,即其后来所提及的朗读要比其原先的默读更具完善性,这种暗示同样能够解释 Giovanni 为何回应说共同的朗读会让他/写作者与她/阅读者更为亲近(即便这句话在表层的文本上同样不会产生理解的困难)。
而正是妻子 Lidia 在片末长达几分钟的书信朗读里,我们注意到了原先那仅仅被提及却未被实现的朗读的动作,由于其先前的明显失位所造成的残缺性,这样的动作在此时明显要更能引人注目。朗读的动作势必与人声相伴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朗读蕴涵了人声。因此,被我们所注意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动作,还是一种声音。甚至我们也许可以说,人声在这个时候所拥有的在场感是超过其他任何元素的,毕竟,真正长达数分钟的,不是被镜头所切割的同一动作的各种被展示侧面,而是连续的朗读的声音(若从不可分割性上说,至少比起前者,它也许才是真正的绵延)。倘若以一种修辞的手法问在这一场戏中谁是真正的主角,那么回答说是声音也并不为过。
实际上,在这场戏的主角真正出场前,Lidia 就已经为这一时刻做了准备:
 Lidia 在朗读前对画外音乐的不满
Lidia 在朗读前对画外音乐的不满此时画外的音乐演奏在二人刚走出别墅时便已出现,而当他们离音源越来越远时,这一音乐成为了二人的背景。然而,在 Lidia 终于要开始朗读前,她似乎要打破这一声音的秩序,而其言语-动作又肯定了(或者说指示着)声音的存在。因此,当朗读的人声成为主导时,我们对其产生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前期准备所导致的,朗读声本身意味着一种新的声音秩序的完成。
需要提及的是,Lidia 的人声成为主导,这是在其作为观看者的身份几乎被完全解构的背景下发生的,换言之,她在这里的人声与视线恰恰处于有与无的两端。而既然她的观看主体性是逐渐被侵蚀的(病房-泳池-草地),一种寻找先前的对 Lidia 人声的强调的心理倾向便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根基的。有趣的是,在最后一场戏以前,Lidia 的人声确实得到了(至少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次强调,而此时恰恰是她因丈夫坦白而第一次得知他出轨之后所做出的一次逃避/出走。确切来说,这场戏中的声音——而最终是人声——同样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当发现她并不在家时,丈夫拿起电话筒,试图通过声音来与 Lidia 重新建立联系,但因为并不知道她在哪里,因此只能作罢,向阳台走去,而声音也正是在此刻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吸引着我们:
 一个让我们确认 Giovanni 所在的物理高度的仰拍镜头,与之相伴的却是着高跟鞋的匿名主体步行时所发出的高响度的声音
一个让我们确认 Giovanni 所在的物理高度的仰拍镜头,与之相伴的却是着高跟鞋的匿名主体步行时所发出的高响度的声音 当高跟鞋的声音在镜头切至楼上时依然保持同样的高响度时,一种因不匹配而产生的怪异感吸引着我们对这一声音本身(以至于其所暗示着的女性主体)的注意
当高跟鞋的声音在镜头切至楼上时依然保持同样的高响度时,一种因不匹配而产生的怪异感吸引着我们对这一声音本身(以至于其所暗示着的女性主体)的注意即便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声音究竟是由谁发出的、与 Lidia 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它的确与 Lidia 存在着某种关系。毕竟,紧接在这一高跟鞋的声音之后的,便是指示着 Lidia 的电话铃声的出现(此前电话以被触摸的形式出现了一次):
 Lidia 的人声在片中第一次先于其视线
Lidia 的人声在片中第一次先于其视线在电话被 Giovanni 接起时,尽管我们没有直接感知到 Lidia 的人声,但它至少也以某种方式让我们知道了其此时的存在,且按照这种方式,我们并无法知道视线是否在这时候同样存在。换言之,从我们(包括与 Lidia 通话的 Giovanni )的角度来说,此时 Lidia 的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观看无关的,相反,它与 Lidia 的人声/言说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此时人声主导的情形与片尾一样,都发生在她面对——而非仅仅是经受——丈夫的出轨对其所带来的伤害的时候:在第一次得知 Giovanni 出轨后,经过一种下意识的逃避(关于这点后面会详述),她终于重新与他建起联系,而这一联系最初便是人声的;而当目睹丈夫的另一次出轨后,她同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逃避式疗愈后决定面对他,但这一次明显比之前更为彻底,她做好了结束这段关系的准备,而这一结束动作的发起,同样依赖于人声,依赖于她对丈夫曾经写给她的书信的朗读。当然,与婚姻关系的破裂程度相应,虽然这两处都是以人声为优先的,但后一处的程度明显要更高,不论是从其被我们所知的方式的直接性来说,还是从其持续的时间长度来说。当人声取代视线从而成为 Lidia 的本质的新的指向时,与婚姻的破裂相一致的某种取消就变得尤为明显,毕竟,在如前所述的一种前设下, Lidia 原是观看的主体。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取消同样是渐进的而非瞬时的。
也就是说,在 Lidia 与 Giovanni 的婚姻中,情感关系的变化是清晰的而非含糊的,只不过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表层的文本。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角色的台词是否可信。至少,如果我们从 Lidia 这一角色来看,台词在很多重要的时刻似乎都不太可靠,毕竟在每次得知丈夫出轨时,其言语表达的倾向常常与其行动的意味相反。
 第一次知道丈夫出轨时,Lidia 在表面的语词上透露出异常的不在意
第一次知道丈夫出轨时,Lidia 在表面的语词上透露出异常的不在意
 然而在选择远离丈夫时,Lidia 相当反常地向路遇的男性抛出笑容,这看起来更像对丈夫的背叛无法释怀
然而在选择远离丈夫时,Lidia 相当反常地向路遇的男性抛出笑容,这看起来更像对丈夫的背叛无法释怀丈夫的出轨对于 Lidia 来说,并不像她的言语所暗示的那样,是能够轻易被她所忽视的。在出走的过程中,她注视其他男性的目光,以及那对路人本不必要的热情笑容,让我们知道她对丈夫的背叛相当在意,而在另一方面,此时的她又不希望结束这段婚姻关系,因此她只能试图向外寻求排解的出口,通过做出点什么来实现心理代偿(当然,道德感极强的她实际上并没有以同样的背叛来回应丈夫的出轨)。而在目睹丈夫的第二次出轨时,她下意识做出的行动依然首先是逃避:
 在怀疑丈夫是去找 Valentina 后,对于陌生男人来说鲜少得见的 Lidia 的笑容再度出现
在怀疑丈夫是去找 Valentina 后,对于陌生男人来说鲜少得见的 Lidia 的笑容再度出现 在面对丈夫和 Valentina 时,她的言语再次表达出一种对丈夫出轨的不在意
在面对丈夫和 Valentina 时,她的言语再次表达出一种对丈夫出轨的不在意Lidia 对丈夫两次出轨的反应,若仅从言语上观察的话,与真实明显是有所偏离的,这也使得表层文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靠的,我们并不敢对角色所说出的一切持完全信任的态度。但,Lidia 的声音中总归有一些东西是值得相信的,可那至少在最初的意义上不是她自己的言说,相反,那是她对丈夫以往的文字的朗读,只有在将对方的语言变为自己的声音时,她才真正坦诚地面对着关系已经被不可挽回地破坏的事实。而如果从另一个(与上一部分相联系的)角度看,之所以在此时她所说的话语具有真实的力量,也是因为,不同于先前(第一次出现人声主导的时候,从她口中说出的依然是表明自己不在意的谎言),如今的她所拥有的也仅仅只是声音了。
相比起言语,身处于关系之中的主体的视线减弱及其人声的相应强化更多地与真实的情感关系变动有所联系。但这可能不是全部的真相,或者说,也许更为根本的事实是,在《夜》中真正被感知到的,最终只是两种倾向:一种是建立,而另一种是消解。它们作为片中最原初的两种要素,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既是视觉与听觉的,又是文本的;也许我们在其中所捕捉到的一切变化,最终都只是这两种倾向,它们主导着所有具体的、细微的东西的运行,无处不在又贯穿始终。
© 本文版权归作者 Summum Bonum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