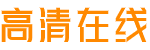光圈内外
——场名为梦露的幻梦的生成机制
一、菲勒斯与好莱坞
劳拉穆尔维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以这篇论文为分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关注点从电影成品的创作特征转移到了电影内部的运作机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电影与观众之间的心理关系上了。为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进入电影理论领域奠定了基础。
如你所见,这是一篇为《金发梦露》这部电影正名的影评。对于很多指责本片“男性视角剥削女性”的评论,我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引述这篇论文来论述本片的立意恰恰与这种指责相反。
穆尔维指出,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下,女性作为缺乏或被阉割的状态进入符号系统的,体现在好莱坞故事片中,则是男性作为主动的观看者,女性作为被看者。当电影中的男性得到和占有女性的银幕形象,观众也通过观看间接得到或占有了女性的银幕形象。好莱坞的主流故事片就通过把银幕内男性视线和银幕下观众视线统一起来的“技术手段”,加强了叙事的逼真性和沉浸感。
而在本片里“在技术上统一男性角色视线和观众视线”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不可能。本片的男性角色没有一个能让观众有认同感。恰恰相反,观众可以清晰看到他们对于诺玛的不同程度的剥削。而对于诺玛对男性的欲望,我们同样可以效仿穆尔维,从精神分析里找到答案
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孩子一开始都欲望母亲,却被父亲的介入阻断。孩子此时便认为父亲拥有一种叫作菲勒斯的东西,正是父亲拥有菲勒斯才能赢得母亲的欲望,所以男孩和女孩都渴望菲勒斯,但是问题在于菲勒斯是不存在的。男孩最终的解决之道是假装自己拥有菲勒斯。而女孩作为“被阉割”的存在明白自己是不可能拥有菲勒斯的,于是选择成为菲勒斯,尽量让自己变得与自己的母亲同一化转而欲求父亲,这也就是女性气质的来源。
对于诺玛来说,父亲的存在既不可捉摸却又实实在在掌控着母亲的欲望。她渴望成为父亲的欲望对象,却因为无法了解真正的父亲,无法得知自己怎样成为菲勒斯。就像诺玛对小卓别林兄弟所说的那样,至少有父亲的人知道自己是谁。言下之意,她需要一个父亲来定义自己是谁。

而对于诺玛来说,关于父亲的唯一线索,就是童年时期父亲的照片。父亲在照片中的形象也正是经典好莱坞男明星形象:
 父亲的照片
父亲的照片 好莱坞黄金时代男星克拉克盖博
好莱坞黄金时代男星克拉克盖博恰巧父亲也曾在好莱坞片场工作。诺玛实际上把父亲等同于了旧好莱坞电影的典型男性主角,而为了成为这样的“父亲”的欲望对象,她选择成为这样男性主角的欲望对象——被动柔弱的女性主角,选择成为玛丽莲梦露。而穆尔维指出在主流叙事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存在着男性主动、女性被动的“两性分工”叙事结构,也就是男性主导叙事而女性则是被动的、被凝视的形象。所以在许多观众眼中被动、不知反抗的玛丽莲梦露形象反而在本片中作为一种高级的反讽而存在。
而回到我们刚才说的男性角色,小卓别林这个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以“父亲”的形式)确实主导了叙事,但是他的行为目的交代的是如此不清晰,我们只知道在“父亲”的问题上他和诺玛两个人存在着共鸣,他似乎为了弥补父亲过于强大让自己无法活出自我的遗憾选择成为诺玛的“父亲”来给诺玛的人生下一个定义。但是却没有更多细节来表明他行为背后的目的。引用穆尔维的原话:“当观众与男主人公认同时,观众就把自己的观看投射于同类身上,亦即他在银幕上的代理人,从而使男主人公对事态的控制权与色情观看的主动权相结合”。小卓别林自然承担不了这个代理人的功能。而梦露的后面几位伴侣也不行。
梦露的第二任丈夫更是把“占有”这个属性拉到极致,影片专门有一个镜头,诺玛的第二任丈夫向诺玛求婚后,镜头从一个类似于银幕的东西那里拉出来。表示这是传统电影中对被动的女性的“占有”


就像一部好莱坞的浪漫爱情片的结尾,两个人甜蜜地在一起了。但是电影却专门强化了这种“占有”的概念,在之后的情节里,第二任丈夫因为对她的占有欲不断地对她进行暴力行为,甚至在求婚时握着脖子的动作在之后的情节也变成了暴力行为的一部分,构成了一种巨大的讽刺

诺玛的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对于诺玛同样是在“占有”,只不过他“占有”的方式是把诺玛/梦露当成写作的灵感源泉。肯尼迪总统更不必说,电影直接把“玛丽莲梦露给肯尼迪口交”拍成了在影院放映的画面,讽刺效果明显

电影中的任何男性角色都无法成为观众的“代理人”,因为根据穆尔维的表述,让观众认同的男性角色应当是更理想化的自我,而这在本片已经成为了不可能。而在观众视线和男性视线已经无法统一的前提下,电影又实实在在把这种男性角色对于被动女性的“占有”拍了出来,这就产生了间离性,让观众无法跟着他们占据女性角色,进而对这种传统的男性符号系统产生反思。
不过以上似乎也并不能完全证明本片就对诺玛简/玛丽莲梦露没有剥削。本片的女主角似乎依然是被动的、缺少成长的、不知反抗的女性角色。穆尔维在评价斯登堡的电影时就指出斯登堡的电影并不依靠线性时间、男主人公视线等手段,而是创造出“最终恋物”,把女性这种阉割威胁者看做是可恋之物。很多观众批评本片时也表述出对这种物化梦露的行为的不满。那么,这种指责是对的吗?对,也不对。在电影中诺玛/梦露确实作为被动脆弱的形象出现。但已经论证了男性结构是一种反讽之后,我也将在此论证梦露的形象也是一种反讽,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光圈说起。
二、注意圈和第二自我
在梦露和一群演员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老师模样的男人讲解了这么一个概念: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很困惑:这个光圈是什么?封在光圈里和创造角色有什么关系?
答案是注意圈,一个表演上的概念
注意圈的概念出自斯塔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第五章,注意圈是戏剧舞台上用打光打的一块范围(这个范围之外则是一片黑暗),演员会注意这个范围的各种对象,但注意力不能跳脱出圈外。这种做法是为了让演员集中对舞台上对象的注意力,完善表演细节。
而在电影中注意圈或者说光圈的概念可以说反复出现。影片的一开头电影灯具的打光就可以视作是注意圈的体现


光圈/注意圈和摄影机的联系也是一直在暗示,“老师”开始介绍光圈的镜头的转场正是和摄影机的联系:



光圈/注意圈在文本中也和堕胎联系起来,诺玛第一次堕胎和最后一次堕胎,光圈/注意圈的意象都有出现:


光圈/注意圈这个意象的出现贯穿始终,远远不止我列举的这些,那些拍摄诺玛的相机、诺玛身边的医学灯光都可以算进去。但是不妨让我们先探讨一下这一意象代表着什么。
诺玛和第二任丈夫结婚后她和现实中男方的家人可以说格格不入。在百般不适应后,诺玛问丈夫怎么和真实生活的人打交道,丈夫引用了拳击的概念,告诉诺玛一切都关乎注意力:

但这个男人不知道的是,在关于表演的教学中,其实集中注意早就被教导过。然而对于真正的生活,诺玛却始终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在注意圈之外的黑暗是不需要被关注的,所需要关注的只是那一小部分范围。在这一部分范围中诺玛扮演着玛丽莲梦露这个举世闻名的角色,而注意圈之外灯光照不到的黑暗,不是诺玛的考虑范围。所以每次她进入现实生活的努力最终都以她必须成为梦露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诺玛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却又必须成为父亲的欲望。而对于她的两任丈夫,她叫他们“daddy”,却都明白这不是她真正的父亲。她只有去那片童年记忆里的好莱坞去寻找她应当怎样成为菲勒斯,寻找她的定义。
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是诺玛看着街上的每一个人叫他们父亲,但是对于自己真实存在的丈夫阿瑟米勒,她却只看到一张模糊的脸


这就是这个角色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光圈/注意圈之内她扮演着被动而脆弱的性感女郎,光圈之外却是一片模糊。而她不仅被和她演对手戏的男性主角所“占有”,而且被银幕下的观众所占有。这就是所谓“凝视”的本质:当她选择成为“好莱坞父亲”的欲望客体的时候,她也就成为了所有观众的欲望客体。这些对她而言一片“模糊”的观众却在实际上占有了她
而对于观众,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劳拉穆尔维指出视觉快感之一就是自恋快感。穆尔维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被识别的影像被认为是自身物体的反映,但是错误的优越识别却把这个身体作为理想的自我而投射到自身之外,一个异化的主体,于是引起随下一步及与他人的认同”,这也就是好莱坞明星制的基础。而那些作为主体的男明星能够成功,作为客体的玛丽莲梦露也自然作为明星被纳入了男性的符号秩序之中。
在这里,我们来引入另一个表演上的概念:第二自我
引用《电影艺术词典》的定义:
演员创造角色时具有“双重自我”,必须过好“双重生活”:一方面作为演员过着创作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作为角色过着形象的生活。演员表演时第二自我(角色的我——形象)在哭、在笑、在愤怒、在欢乐,同时第一自我(演员的我——创作者)构思、设计,然后由第二自我(角色的我)体现出来。演员如果缺乏自我控制,以致于激动时哭得忘了台词,忘了接戏,甚至愤怒起来真的去伤害对手,那么表演将告终止,表演艺术也随之消失。所以表演的分寸、表演的魅力、表演的艺术也就产生于这种“双重生活”“双重自我”的微妙的平衡之中,第一自我的支配力也就越强,艺术家的表演功力也就越深。
而诺玛简何尝不是在扮演玛丽莲梦露这个角色,而玛丽莲梦露正是诺玛的第二自我。这个第二自我是菲勒斯,是梦露想要成为却没能成为的东西。所以她才会在一次次说“她(玛丽莲梦露)不是我”,却又被框在这个注意圈里,无法去真正发现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只有在好莱坞的幻梦中把握着自己的定义。拉康认为,女性是“乔装”自己是菲勒斯。而在这里,诺玛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成为玛丽莲梦露。直到父亲变成幻影的那一天,直到发现菲勒斯不存在的那一刻,一切都走向了毁灭和虚无。
三、元电影和元表演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在本片的描述中,玛丽莲梦露这个形象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叫诺玛的姑娘欲望父亲却不了解父亲,所以只能根据好莱坞的线索变成好莱坞典型男性主角的欲望对象,最后变成这样男性主角的欲望对象——一个旧好莱坞典型的被动柔弱的女性角色。而根据劳拉穆尔维的理论,她又不只是被占据主导的男性所占有,更是被观众所占有。所以梦露的一生是一直被剥削的一生。而本片首先通过专门展示出男性占有却又无法让观众认同男性占有的方式已经打破了传统叙事性电影的剥削结构。
而对于观众本身的视线,我们又可以看到许多“展示”:梦露和肯尼迪的画面被放上大银幕、各种影院内镜头的展现和银幕说内容交织银幕上的诺玛产生的互文、电影画幅从学院画幅到遮幅宽银幕的变化甚至是各种摄影记者拍摄明星玛丽莲梦露的过程。都体现着观众视线以及摄影机本身对于诺玛/梦露的剥削,这都让我们这些观众无法认同剥削,反而在电影中清晰地看到剥削的机制并进行反思。穆尔维提出打破视觉快感要让观众产生间离意识,有解放摄影机的观看和观众的观看。而在电影中“诺玛简扮演玛丽莲梦露”的“元表演”和“展现旧好莱坞叙事电影所代表的男性符号秩序对女性占有过程”的“元电影”,我们得以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好莱坞对于女性剥削的机制,并由此进行反思。我们最后也都会明白:菲勒斯不存在,而好莱坞,这片璀璨而光鲜的地方,也不过是心碎之人的一场幻梦罢了。
 © 本文版权归作者 发条巧克力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本文版权归作者 发条巧克力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