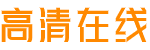吃人的礼教,吃人的社会。
眼看着李二毛从一开始眼里有光、勇敢坚持自我的跨性别者、沦为后期空洞麻木、不断自我怀疑的“人妖”。这过程中经历了大众对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强权对弱者的剥削和压迫,来自亲密关系的背叛与伤害,以及旁观者的嘲讽和冷漠。即便生出有一双蓬勃有力、飞向新世界的翅膀,也在底层社会因循守旧的运作下碾为碎沫。
李二毛是一个复杂的欲望载体,他时常猜忌怀疑,却渴望坚定且真诚的被爱;他不屑世俗标准,却期待融入并拥有平凡生活;他追逐富足美满,却也甘愿为了及时行乐一掷千金。他是平庸,也是不凡。是犹豫,也是果敢。是清醒,也是更深处的迷惘。影片通过时间刻度将这种成长之痛很具象地表达了出来,虽然违背了纪录片的“不干涉”原则,却用陪伴者的视角将现实故事阐述得尤为血肉淋漓。
不可否认的是,镜头的记录和第三者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故事走向,以及李二毛在生活动荡前的自我选择。几场略显戏剧性的争吵,和车里的表演型自怨自艾,让观众很难不怀疑这些情绪究竟是李二毛的真实所想,还是为了装潢他敏感脆弱又多情的“女性”人设。内因不可究,但把一个揣着普通梦想的人逼上绝路的外因,却是证据确凿。
面对社会规则,李二毛已再三退让。他放弃了出唱片当明星,放弃了浓妆华服笙歌艳舞,放弃了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甚至放弃了通过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到最后仅存的小小愿望,不过是和爱人在乡野田间拥有一个塑料布搭起的家,做一对普通的农民,不打扰任何人地过完这一生。
可就连这样,带着有色眼镜的看客们也不允许他实现。只是因为他不一样,因为他“不男不女”,所以默认他不配。何其讽刺,不偷不抢、靠双手吃饭的李二毛和村民口中靠拐卖妇女和贩卖儿童致富的二毛父亲相比,竟是个一事无成的懦夫。
被迫用六百块钱卖光了老家的地产后,李二毛回到深圳,躺倒在二十块一晚的旅店床上,向自己、向镜头、也向观众提出了那个最无奈的疑问:世界这么大,究竟哪里才容得下我?
爱是他最后的避难所。从小背井离乡,他需要很多很多的爱来证明自己被需要,证明自己仍有活下去的牵绊,只要有爱就不算完,爱人在,家就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男人里,小江带给他安全感,小龙给予他陪伴。爱人的怀抱和酒精毒品赌博一样,都是他选择麻痹自己暂时逃离世俗的方式。所以当爱人一个接一个离去,李二毛坚守自我的内心防线也在一点一点被攻破。当他身后终于空无一人时,退一步便是被流言吞没的万丈深渊。
李二毛没有等到那场梦中的婚礼,没能穿着婚纱像正常女人一样步入圣洁殿堂。他的归宿在工厂流水线,一个歌颂妥协,合群,和顺从的地方。在那里他剪去了蓄起多年的长发,含胸驼背地藏起了作为“女人”的全部痕迹。千百个艰难维生的日日夜夜里,恨与爱一并变得毫无意义。已然两手空空,李二毛别无所求,也不再害怕失去什么。
查出HIV的时候,他盯着窗外倒退的风景,轻声说道,“我想去趟香港,我想要平静”。摘除假体恢复男儿身后,他摸着前胸喃喃自语,“跟了我这么多年,突然没了,空落落的。” “不过我可以正常去游泳了,像个男人一样。”
不知道那个夏天他有没有痛快地游一场泳,洗涤多年来身上背负的污言秽语也好,道德枷锁也罢,只是漂浮在炽热的阳光下,赤条条地做回自己。
李二毛的一生是双面的,不过不是男女分别,而是生存状态,要么热烈地活,要么平静地死。如果九泉之下真如他所说的那样更加包容,他可以和爱人团聚,被亲人接纳,为旁人所理解,那么我庆幸他终于逃离苦海,重获新生。
希望那里有一条没有尽头的马路,在暖烘烘的路灯照耀下,她依旧穿着那条带着嫩黄色翅膀的裙子,踩着高跟鞋肆无忌惮地奔跑,永远赤诚,永远鲜活,永远美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