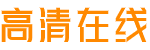正如《金发梦露》在剧情层面重复强调一种极为刻板、单一的含义(恋父情结)来为人物的一切归因,多米尼克的影像逻辑也是基于刻板的单一含义:每一种技法都通向一种单一的情绪、单一的理解和单一的印象。电影的很多时候,夸张的镜头角度、光线、色彩或音乐看似在心理和生理层面连接了观众与梦露,让我们能所谓“感受到梦露在男性目光下和男权社会结构中的压力”,但其实仔细想想,如果不是建立在详实的叙事所能达成的充分的理解和移情效果的基础上,光靠一些花哨的电影技巧,怎么可能做到让一个人体会到另一个人的感觉?除非是,将一个人心理和生理的一切,都用一种最扁平化、夸张化、绝无法产生其他解释可能的手段,来粗暴地输出给观众。
这就是《金发梦露》所做的。因此这部所谓的传记电影根本没有“人物”,梦露不被承认为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被肢解、化约成了一系列的单一的、简略的含义,导演通过将这些含义影像化,让我们以最直白的方式去洞悉她的一生。在这一方面,《金发梦露》像卡萨维茨式电影的反面,或(在分享女性受到的苦难方面是)《旺达》的反面。卡萨维茨和洛登同样试图让我们与人物打通心理和生理的通道,但这种通道是以漫长的前奏中充分的情节和表演的铺垫为前提,让一个人物在我们的心中不仅留下已知的印象,而且留下了未知的疑惑和神秘,这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无法被化约为单一含义的人物。在这之后,电影才能制造出爱的激流和旺达的一瞥。多米尼克则试图在短时间内就靠花哨的技术创造出一个个极端的情绪碎片,但这些碎片能拼凑成一个人物吗?
电影中的人物,是不可化约的、不透明的、观众可与之平等对话的个体,只有在(不只对观众,甚至对创作者而言也一样)不可化约、不透明里才能生成真实,不然只有“编剧”。对于编剧,就算他编出再多细节,你能相信什么?就像阿莫多瓦在《平行母亲》的最后“假设”了一次真实的历史挖掘现场,《金发梦露》“假设”了一个真实的梦露——除非是对叙事毫无自觉或者只为猎奇的观众,否则很难想象能从这些假设中获得任何东西。
Anna的表演在这部电影里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常因此而产生一种尴尬的多余感),因为没有人物,没有我们与人物的距离(想象一下,电影号称提供的那些体验,其实更适合做成第一视角的VR游戏,甚至比这更接近生理的媒介——比如一种类似于模拟分娩疼痛体验器的、可以模拟男凝压迫的仪器,否则谈什么分享感官,不过是视觉消费而已),没有观众与人物对话的空间,演员的表演也就不是在力图创造一个可信的、真实的人,而只是配合各种各样的电影技巧去传递单一的含义,顺便也将自身给单义化了。
如果没有创造出人物,那么一部叙事电影(何况是一部号称以真实人物为基础的传记片)中就只剩下虚假,只剩下表面展现出的最单义的指向,而这些指向的依据不过是导演对人物独裁式的定义,无论这种定义多么复杂、多么反传统,都一样是独裁。因此《金发梦露》确实就是将观众捆绑在发条橙式的刑具上观影,在难熬的三小时内,你不得不接受导演对于梦露的一切深入到心理最深处的定义和刻画(多米尼克在这里以弗洛伊德为借口把一切都解释得如白痴般简单,太恶心了),但他甚至懒于、或者根本没有能力为这些定义建立证明:试看影片中段梦露与剧作家丈夫的见面一段,这是这部电影碎片化的叙事为数不多的长段落情境。虽然导演用投机取巧的办法跳过了情感的决定性瞬间,但在后面的二人在酒吧谈话戏中,他彻底暴露出了自己根本无法正经地描述人物的行动和情感(Adrien Brody装模作样地哭的时候我简直都快笑出声了)。
《金发梦露》在视听技术上投入的大量成本,只是进一步的保证了这些单义的技法更加单义(比如在已经非常直白粗暴的戏上再叠上一层情绪操纵式的音乐),并且让这样的单义美化地让人难以察觉(比如,开头Norma母亲毒驾时的表演已经做作和空洞到了难堪的地步,但因为特效分散了注意力,所以才能勉强忍受)。并且,多米尼克在技术层面不断追求繁复冗杂的“美”,让人觉得这些技法的存在甚至根本不为指向什么,而只是在反射自身的壮美。如果要定义油腻自恋的作者电影,没有哪部比多米尼克的这一部巨作更合适的了。
最后再回到女性主义层面的疑惑上。我本来根本不想浪费时间讨论这个,因为它在美学上的粗滥和人物塑造上的独裁性早已暴露了创作者的鸡贼。但这里想指出一点:如果《金发梦露》中大量剥削式的镜头难以被判断为是批判还是消费的话,那么多米尼克所刻意设置的、与这些剥削镜头对立的代表梦露生活“美好希望”部分的镜头,几乎全都在堆砌一些腐朽的意象和视觉,比如海滩、白裙、玫瑰,这些无疑是多米尼克的男性想象中的浪漫;甚至,梦露的台词直接指明了,她想要简简单单地生活(作为好莱坞漩涡的反面)——指生养小孩、做家庭主妇。从我们已知的史实看,仅仅用这些去定义梦露的幸福,比消费梦露的苦难的嫌疑要更加值得警惕。
© 本文版权归作者 Annihilator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