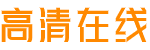下午去联合广场附近的一家店铺修电脑,按着预约的时间过去,却始终找不到在手机上提前标记好的地点。倒也不慌不忙,就慢吞吞地在街上晃悠,四五点钟的阳光不算热烈,偶尔还有一阵风,旁边刺槐的阴翳里立着个嬉皮士打扮的年轻女生在孤伶伶地唱着爵士乐,声音不大,也听不确切。问了几遍周围商家的店员,才寻到入口。那是一扇窄窄的铜门,拉开门拐进去还得爬上三层,店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气。接待我的是一个印度男孩,他接过电脑,有模有样地插上东西,问起电脑的型号和年代。我对这些也没什么概念,就指着电脑说:“大约很久了吧,你能在设备上查到吗?”他又摆弄了一阵,突然皱起眉头,随即扯掉那些线路,把电脑递还给我,说:“不好意思,我不能帮助你,这个电脑太旧了,苹果已经不生产这个型号的零件了。”他形容“旧”用的单词是ancient,我不禁笑了起来,又问道:“那还有机会卖钱吗?”他看着我,凝重地摇了摇头。“太旧了,没人愿意要的。”“卖给博物馆呢?”他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起来。
从店里下来,又回到了广场。临近离开纽约,和美伦说好见面聊聊天,也就顺便约在附近。广场深处有个小公园,零零散散地摆着明黄色的桌椅,边上有个老爷爷在吹萨克斯。他带着整套音响,吹的曲子多是一些经典的欧美流行乐,靠近听时颇为气派。一曲终了,他便提着帽子挨桌挨桌地来要打赏。因为不想被太大的音乐声打扰,我挑了处靠边的椅子休憩。不远处坐着位正戴着耳机看电脑的中年女性,老人把帽子伸到她眼前,晃了晃,她有些疑惑地摘下耳机,和老人对视了一阵,然后仿佛明白了什么似地掏出钱包里的零钱,放进帽子里。
阳光透过树叶打下翕动的阴影,看了一阵子手机,眼睛被晃得生疼,索性就靠在椅子上,盯着前方的树与雕塑发呆。于我而言,纽约最值得喜欢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公园,或大或小,陈设不复杂,却总有种奇妙的感染力吸引我坐下来慢慢感受。公园的地面总是脏的,散落着发黄的落叶,或者用粉笔涂画着各种图案或宣言。人流是适宜的,即使是最热闹时,每个人也能默契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地盘,在一起相安无事地闹腾:一边在弹着古典钢琴,一边在跳韩国kpop,一边在卖廉价工艺品,一边在做有关身体的行为艺术,一边在高声发表演说,一边在表演杂耍魔术,一边在草地上铺着地毯晒太阳,一边踩着滑板呲溜从身侧穿过……
当我正观察一根立柱基底的浮雕入神时,美伦衬着深蓝色长裙走了过来。和她在公园里坐着聊了会儿天,又慢慢散步到旁边一家日法风格的甜品店,边吃边闲聊。说起马上要回国了,“你说成都这封禁要是持续下来,机票被取消,我会不会在香港滞留然后被遣返回美国;然后美国看我没有身份,也不让我入境,于是又把我遣返回中国,”我开着玩笑,“然后,然后我就成了太平洋上的游民和幽灵。”美伦接了下去,“哈哈哈,我已经想好了一本小说的情节设定,就是到了2025年,太平洋上一些无主的岛屿人满为患,全部都是像你这样无家可回的游民。”我笑了起来,又叹了口气。顿了一会儿,“你有时间可以去看一部电影,叫《椒麻堂会》,最近在纽约有放映,是关于你老家的,听说还不错。”我有点好奇这个怪异的名字,打开手机搜了搜,附近的Anthology Film Archives正在放映,时间恰好是今天晚上。“好像就是在今天欸。”我把手机翻过去给美伦展示。“要不现在就去,马上开始了。”“好啊。”美伦利落地应声。
入座时电影已经开场了一阵,荧幕上的老乡正咿咿呀呀地用家乡话唱着川剧,布景里云蒸雾绕,表演的人又浓妆艳抹,仿佛在一个古老神异的时空里漫游。故事开始于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四川,热爱听剧的刘旅长创办了新又新川剧团,招纳了一批年轻演员,时间线一直延续到文革,电影也就围绕着剧团以及剧团里的孤儿邱福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生活变迁展开。
二十世纪前中叶的时代更迭是中国人熟悉的母题,革命、战乱、鸦片、饥荒、文革——电影叙事也行进在这条前人反复实践、略显拥挤的轨道里。但《椒麻堂会》历史书写的内核却是别致的,或者说生猛的、热闹的、粗粝的、草根的、怪诞的、幽默的,带有一种属于川渝地区的魔幻现实主义气质。其中熟悉的交流方式和世界想象常让我想起老家的乡土社会,那里的神明是拟人的,死亡是共存的,暴力是戏谑的,伤感是在酒里流动的。想起几年前老人去世,在农村老家举行七天的仪式,请来道士和尚在后屋里念诵经文,又请来乐队师傅敲锣打鼓吹唢呐,前桌的坝子上搭个台子和棚子,摆着桌子板凳和瓜子花生。亲戚朋友或乡里邻居前来悼念,晚上就坐在坝子的棚下搓麻将。入葬的前一天晚上还有演出,剧团里有个反串角儿,披着金黄假发,穿着黑色丝袜,趁着当时流行的凤凰传奇音乐跳舞,他(她)的动作幅度也夸张,每一次露出底裤台下便响起掌声。待到第二天清晨天没亮,送葬的队伍开始启程转山,长长的队伍举着火把在田埂上连成条线,火光对峙着夜色,在远处的鸡鸣声里一簇一簇地跳动。
也会想起家乡的食物,就像电影名字所暗示的,有关故乡的记忆与味觉的感知相互纠缠。从一开始馒头稀饭花生的味道,小邱福顶着个空碗排着大锅饭的队,“我怕我不学唱戏被赶出去没饭吃”;到鸦片的味道,烟气氤氲里四处漂泊,又相互联结;到坝坝宴的味道,剧团重聚,开席庆祝,“全是花椒,换一桌”;再到饥饿的味道,唱戏换来屎与蛆的所有权,烤熟捣粉,冲开水喝,或者得来个瘦削的南瓜,不忍地把孩子送回给亲生母亲;最后过奈何桥前,也是吃了一顿又一顿,总得大口吃饭,大碗喝酒,才走得巴适。川菜重油重盐,那些有关味道的记忆仿佛浸润在洒满花椒的油水里,鲜活地翻滚。即使是不曾体验的饥饿,也勾连起儿时奶奶讲故事,不经意提起姊姊妹妹哥哥弟弟饥荒年代饿死时的怅惘。
对于过去的直视与审判常是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的底色,但这部电影却保持着一种幽默的节制,悲哀与疼痛在一种戏剧性的想象和生死通灵的民间信仰里自我消化。政治、战争与死亡不是笃定的,它们在古老的土地上轮回又瓦解;时代里人物却是鲜活的,坚定的,不容置喙的,他们站在历史的幕布里,保留着独属于他们的“密码”,与我遥遥相望,常让我觉得他们就隐没在故乡的周遭,未曾消散。有别于伤痕艺术的反思与展望,它呈现出一种连续的亲近的历史,我们与前人似乎从未割离,不过是行进在道路的前后,代际轮替,经济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共享的文化基因却镌刻在最深处。但这也令我感到惶恐与警惕,好像置身于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后疫情时代里的种种温情,种种残忍、种种荒谬,与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温情,种种残忍、种种荒谬仿若隔空对唱——我们缅怀着历史,却也从未走出过历史。
电影终场,已临近午夜。纽约的街头依然灯火通明,却也沉静了下来。“感觉怎么样?”美伦一边打开手机查回家的路,一边问道。“看得有点饿”,我想了想,“也不是饿,就是看着他们没饭吃太饿了,想把自己吃撑。”“哈哈,想吃什么?”“椒麻糖鸡。”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个奇怪的词。“那是什么东西?”“不是电影的名字吗?”“人家叫《椒麻堂会》,好吧。这里离K-town不远,要不找找炸鸡吃?”“好呀。”翻了翻谷歌地图,正好街对面还有家美式炸鸡店在营业。刚过马路还未进入店面,炸鸡的香味就已经远远地传出,把沉浸在历史与乡愁里的自己牵了回来,有些期待,又有些失落地走了进去。后来我想了想,椒麻糖鸡,家乡的椒麻鸡加几勺纽约的糖,异乡的生活约莫着也就是这样了。
© 本文版权归作者 玉溪生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