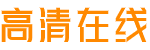自80年代中期始,“历史”便成了大陆艺术电影中萦回不去的梦魇。似乎是一道必须去正视而令人眩晕的深谷,又仿若幽灵出没的、腥红而富丽的天幕。然而,在80年代电影的叙事中,历史却不是一个可以指认出的具体年代,一个时间的线性句段。于是,在80年代的历史书写中,中国的历史不是一个相衔于时间链条中的进程,而是一个在无尽的复沓与轮回中彼此叠加的空间,一所“万难轰毁的铁屋子”,或一处历劫岿然的黄土地。于是,历史成了一个在缓慢的颓败与朽坏中的古旧舞台,而年代、事件与人生,则成了其间轮演的剧目与来去匆匆、难于辨认的过客。在影片《霸王别姬》的故事中,每一个可以真切指认、负载中国人太过沉重的记忆的历史时刻,都仅仅作为一种背景放映,为人物间的真情流露与情感讹诈提供了契机与舞台,为人物的断肠之时添加了乱世的悲凉与宿命的苦涩。诸如日寇纵马驶入北京之时,只是程蝶衣一赠佩剑的背景,侵略者的马队,成功地阻断了段小楼追赶程蝶衣的脚步,而菊仙得以藉此掩起院门,将丈夫遮在身后,将蝶衣关闭在门外;而小楼冒犯日军被捕,则使程蝶衣得到了迫使菊仙“出局”的砝码;日军枪杀抗日志士的场景,只是以连发的枪声、狂吠的警犬、炫目的探照灯、幢幢阴影,只是为遭唾弃的蝶衣提供了一处迷乱、狰狞的舞台;而解放军进入北京,却成了程蝶衣二赠佩剑的景片(直到在文阁那个酷烈的情境,菊仙才得以把佩剑掷还给蝶衣)。面对狂喜的腰鼓队和布衣军人风尘仆仆的队伍,陈凯歌安排了小楼、蝶衣与张公公的重逢。两人分坐在张公公的身边,在为一座石阶所充任的观众席上,目击着这一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缕缕飘过的烟雾,遮断了画面的纵深感,将这幅三人全景呈现为一幅扁平的画面;仿佛在这一历史剧变的时刻,旧日的历史不仅永远失去了它伸延的可能,而且被挤压为极薄且平的一页:昔日显赫一时的公公与永恒的“戏子”,此时已一同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间不值一文的点缀。事实上,李碧华的原作并非一部“多元决定”的、或曰超载的本文,它只是一个关于人生的、关于忠贞与背叛的故事:所谓“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在陈凯歌的影片中,这一忠贞与背叛的主题,则被呈现为“两个女人”(蝶衣、菊仙)对男人(段小楼)无餍足的忠贞的索要,是如何制造着背叛,并最终将男人逼向彻底的背叛。程蝶衣对“从一而终”的苛求,使他一次再次地失去段小楼的爱与庇护,并使自己“失贞”于袁四爷;菊仙为索取、印证段小楼对她的忠贞,一次再次地诱使他离弃程蝶衣、离弃舞台和关师傅的教诲,使他背叛自己朴素的信念、丢弃人的尊严。这一背叛之路将以他对蝶衣的致命伤害及菊仙的出卖与背叛为终点。正是这一忠贞与背叛的主题,使陈凯歌第一次将男人、女人书写在历史之中,以个人(似为中性、实为男性)来充当历史的对立项,影片叙事再度采用了某种经典的电影叙事策略:从历史的毁灭中赎救并赦免个人。在这一贝托鲁奇式的“个人是历史的人质”的主题中,陈凯歌成功地背叛了80年代反意识形态的命题:我们需要灵魂拷问,“与全民族共忏悔”。如果说,李碧华的小说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那么,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正是在空间化的历史与时间化的历史的并置之中,在历史的政治场景与性别场景的同台出演之中,背叛了第五代的文化及艺术初衷。在这幅色彩斑斓、浓烈而忧伤的东方镜像中,陈凯歌们曾爱之深、恨之切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已成了真正的缺席者。纯正而超载的中国表象,已无法到达并降落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于是,中国的历史成了单薄而奇异的景片,中国的现实成了序幕和尾声里为一束追光所烛照的空荡的体育场,成了片尾空洞的黑色字幕衬底。陈凯歌失落了他对历史与暴力的现实指认与立场。事实上,作为第五代“空间对时间的胜利”这一电影语言形态的奠基者之一,由《黄土地》的恢宏、《孩子王》的挫败,经《边走边唱》的杂陈,到《霸王别姬》的全胜,陈凯歌经历了一段不无痛楚与屈辱的心路,一段在中国的社会使命与西方的文化诉求、在历史真实与年代、在寓言式的历史景观与情节之间,陈凯歌曾尝试了一次几近绝望的挣扎与突围。终于,在《霸王别姬》中,陈凯歌因陷落而获救,因屈服而终得加冕。参考:戴锦华老师《电影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