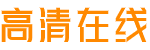首发于:陀螺电影
刚看完《神探大战》时,脑子里闪现的两个字:“癫狂”。创作于2019年疫情前的电影,所散发出的那份无处安放的癫狂感,却是如此对应当下。同时,这也是一部将上世纪港片里那种“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特性,推到极端的作品——脑洞、尺度、表达、场面,年内应该都不会出现其他任何一部华语片,能比它更惊恐、更疯狂、更生猛。
无论朝前看,还是回头张望,你都能发觉《神探大战》在香港电影中所处的一脉相承而又特殊的位置。作为《神探》的“精神续集”,韦家辉与刘青云的组合,没了杜琪峰的规整与收敛,全然呈现出一种时刻处于失控边缘的狂暴与宣泄。

在韦家辉曾经的那些电影《大块头有大智慧》《我左眼见到鬼》《神探》里,他千方百计地植入了主角“见鬼”的设定。鬼,或是人前世的业障,或是人心底的魔障。看似形而上的因果宿命论,其背后的内在逻辑,仍是对社会关系与历史枷锁的多重书写,聚拢回现代人的恐惧与焦虑。
《神探大战》延续了这个设定,刘青云演的“颠佬神探”李俊,不仅能感知被害人的心理,看到人心里的鬼,而且会外化地表现到他的肢体和言语中,构成多重人格分裂的症候。他显然是《神探》里陈桂彬的双生,从沉闷阴郁转向聒噪狂暴,不变的则是如天赋又似诅咒的感知。神探与疯子,也因此被世人划上等号。

电影开篇,快节奏地交待了两起前情:
22年前,屠夫案,阿Sa饰演的女大学生陈仪,被虐待三日后被林峯饰演的“片警”方礼信救下。
17年前,魔警案,重新复刻了《神探》里经典的换枪戏,警察无情地射杀同僚。李俊闯入发布会上,把枪伸进同僚嘴里,企图以鬼上身的方式“还原案情”,但他却成了那个遭受枪击的人。
从此,李俊不再是“警局神探”,而是游走街头,一如《浊水漂流》里的露宿者们生活于立交桥下,疯叨叨地成了一个“街头神探”。桥下写满的,是他对往昔案件的重新推理,在他的判定下,那些案件都是冤假错案,真凶另有其人。
17年后,一个以神探为名的青年犯罪团伙出世。他们用李俊在桥下写的推定,以暴制暴、预告杀人、私刑执法,使得香港陷入到恐惧之中。由此,几方人物开始逐渐纠缠在一起,电影也步入正题。

抽象地说,《神探大战》其实是一场大型的回溯。
《神探》中,杜琪峰和韦家辉曾摄制了大量畸变的广角镜头,构造出倾斜而又鬼魅的香港,以写意的方式呈现出犯罪都市的样貌;《暗战》里,刘德华与刘青云在观塘窄巷里缠斗;《PTU》里,巡警串联起了尖沙咀与广东道;《文雀》里,港岛老街的样貌被照片定格。
而在《神探大战》中,对香港样貌的勾勒换了一个新策略。

韦家辉用近十起发生在香港不同区域的陈年旧案,绘制成一张“香港犯罪地图”——荃湾、油麻地、避风塘、庙街、落马洲、安乐路......
地理位置的背后,隐匿的是时代迁徙下的变与不变。角色们身处在动荡的动作场面中,更是身处在一个个布满历史信息的空间。险境,则意味着历史信息的消逝状态。这是韦家辉本人对于香港的情怀所在,借这些地标空间,找寻香港的当下性与历史间的关联。
而将这块地图串联起的新案,由青年犯罪团伙犯下的,对往昔案件的重演与同态复仇,则是以紧迫的逼视感,让观众不得不去直面时代刻在这些角色肉身与精神上的伤痕。

对于这种伤痕的呈现,最直观的一场戏,是陈仪的第二场裸露戏。她重新回到自己被害的旧地,于遍地肮脏的河渠上,如22年前那样,脱掉衣服,裸露出全身的伤疤。这些疤痕甚至聚集于她那怀孕的肚子上,等待孕育新生。
李俊抚摸那些疤痕,借由身体作为媒介,去感知与推理当日的真相,复原伤害。
这种从肉身指引向精神的伤痕,出现在电影里的每个角色身上,更是李俊这个人物的内核所在。通过感受不同罪犯内心深处的邪恶、冤孽和仇恨,每个人精神的暴力都在不断侵蚀着他,传染给他。

前文提到,“见鬼”的设定,被韦家辉多次使用。而在《神探大战》里,除了延续《神探》中的见人心中之鬼,更是多了一层新设定:见魔鬼。
如罗泓轸在《哭声》中由日韩两国的历史迷局孵化出的魔鬼一般,《神探大战》里的魔鬼被化作一只巨大的蝙蝠状怪兽,黑金色的皮发,露出獠牙。
电影最后,我们才突然理解李俊,他最大的诉求,是世人中哪怕有一个也好,同他一起,看到那只魔鬼,不再孤独——这只具象的魔鬼所汇聚的抽象物,指代的是时代刻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肉身与精神上的伤痕。直面它,看到它,就是看到那些不可看见的、听到那些不可言说的真相。
韦家辉的恶趣味,或者说他的深意在于,他对人性持有的悲观态度。
李俊与魔鬼对峙,他小心地问身旁的陈仪:“你看到了吗?那里有只魔鬼。”陈仪安抚他说:“我看到了。”但每个观众都知道,她没看到。

而这不可避免地导向那个结局,李俊作为“神探”重回警局,仿佛受到了同僚们的重新认可,但下一秒,他就被打断发言,推往整个警局最边缘的位置,望着镜像里自己可怖的倒影。神探的狂躁与孤独、矛盾与痛苦,终究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够看到。
韦家辉借此探讨人心的善恶二元,在片中有多处点明的台词可循。
无论是李俊反复引用尼采的“与怪物战斗的人,小心自己别成为怪物”,还是李俊在船坞怒吼出的“人人都能变怪物,为什么我不能变?我也是人”,亦或是他形容幕后真凶时的“大恶若善,大善若恶”。其实这几句台词都指向一个命题,那就是在当下,传统的正反派对立,已不再能解释我们所处的现实状况。
善恶已然二元统一,难舍难分,无法被一分为二地切割看待。我们对善恶的判断,也不再是做一道选择题。这个命题是这些年来,香港电影在转型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探讨,是《拆弹专家2》里的“我不是疯,我是痛!”同时也是《怒火·重案》里的“我认输,但我不认命!”

某种程度上,《神探大战》能很好地归纳韦家辉的类型创作:从商业性和市场类型出发,从中对每个角色的心理进行深挖,再由心理外化,显露出他对时代的思考。
韦家辉曾说自己写剧本,有点像是做一个“接生”的工作,就像化身为《神探大战》里,李俊在危难之际给陈仪接生。这个接生的过程,即是每个角色孕育出自身与社会关系、自身心理的过程。
也许会有很多观众理解不能,韦家辉为什么非要把陈仪这个角色设计为是一个孕妇。尤其是片中有一幕,陈仪和李俊在跳楼后,李俊把耳朵贴在她肚皮上,未出世的孩子对他说:“我很好,神探加油”。其实,如果把这个孩子理解成是“香港电影”,就能大致明白韦家辉的用意。
香港电影走到今天这一步,很脆弱,也很坚强。作为观众,我们何尝不希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变老的香港电影,现在能很好,现在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