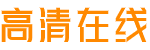在NYAFF做志愿者看的最后一部,是大巧不工的佳作,一下爱上了。但应该如何评论一部蒙古电影呢,在对蒙古电影毫无幻想时。
老板娘Katya的设定太神秘(假)了,这是好事,让我认定她是女主幻想出来的(她们之间少有正常人的互动,通常是一个人长篇大论或者血泪控诉另一个人傻愣着,Katya也是神出鬼没,她似乎有花不完的钱和不会被扫黄的超能力,后来又神秘消失了)(是青少年对于神秘成人世界的那种既艳羡又恐惧之情的投射对象吧,以及蒙古人对西方文化(姗姗来迟的Pink Floyd的70年代气息),连同旧日苏联遗风的远眺?)。
电影歌颂性,但完全不受那些淫秽的符号摆布,既不要porn也不要antiporn,而是拍出了一种根植于生命体验的大乐(女孩化身性爱雷锋,战胜了蒙古的寒冷冬夜和萧条气息,为父母和动物送上春药,让一只无精打采的宠物狗欢脱地流浪),其能量足以治愈一整个文化的性焦虑(不是我说,这种天真,似没有被那些变态美学还有福柯式的权力观”腐蚀“,很少存在于其他东亚国的影像界里,高度产业化的同时是否那些父权笼罩下的性心理也制度化了)。
然而,“性就像说话一样,是要通过模仿其他人习得的”,成人用品售货员少女的初次性探索是大张旗鼓的打扮成兔女郎一个人开房学习使用按摩棒(愚蠢的科技和消费主义文化),并以在长镜头中被子里翻来覆去尝试失败告终。好在她决心在之后的探索中忘掉所学的,返璞归真,一丝不挂地走到傻乎乎的男伴(有hollow, vapid eyes和一个韩国艺名)面前躺下(但没有忘记安全套,非常重要)。
电影里的蒙古人停止游牧了,开始喝咖啡,大谈特谈天蝎座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会话方式(可能是我不了解的游牧民族的文化规范)仍然朴实到可爱,紧张的父母训偷尝禁果的女儿:”我们应该谈谈“,你能想象一个性侵者对目标下手时说的话是”我觉得人类应该互相帮助“吗)。电影外的蒙古人在影院里我旁边摆摊,向观众卖一些羊毛手工制品,说这样可以“save Mongolian economy”,并窃窃私语一些蒙古语笑话。导演本人(清瘦而文雅,有着柔弱的嗓音,大大削弱了作品里的男性凝视观感)和团队把我一介打杂的当成了专业摄影师,让我受宠若惊。我把免费的便携式风扇(来自韩国的礼品,会发光显示”I LOVE K-POP“几个大字母)赠给他们,他们道谢,笑着说这可以帮他们抵御夏日纽约地铁里的蒙古人无法忍受的闷热。
© 本文版权归作者 苦海女神龙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